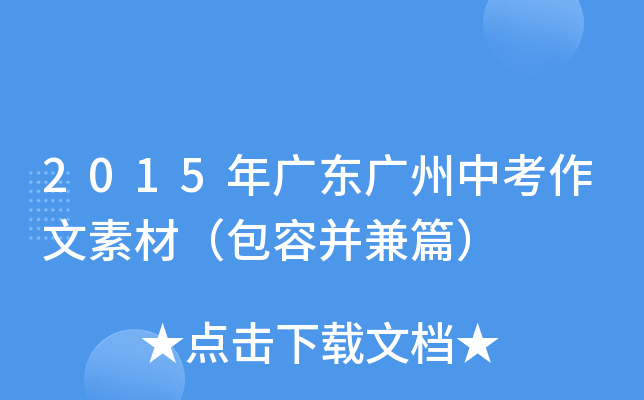广州是—个惹人争议的城市。
争议并非洪水猛兽,往往有提神醒脑之效,它给城市带来观念上的撞击,带来活力和动力。北京、上海也惹人争议,有人看不惯北京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,有人看不惯上海大模大样地把别人锅里的饭都舀到自己碗里,且不管这些看法有无道理,但显然都是出于对北京、上海艳羡的心理,不像对广州的争议,到现在还在争它有没有文化,吃东西的习俗是不是很野蛮,广州人说的是不是“鸟语”,是不是排外等等,翻来覆去,还是两千年前汉武帝时代的话题。
其实,广州从来不是一个排外的城市,从南越国到现在,它一直是个包容度极高的城市,在全国没有一个地方能与之相比。历,广州一直为北方逃避战乱的百姓、流放戍边的罪犯、失宠被贬的官员提供安身立命之所。从广府、潮州、客家三大族群的族谱中,我们都能找到一些“太丘世泽、颍水家声”之类的渊源。
仿佛那些浪迹天涯的人,一踏上广州这片神奇土地,也忽然萌生起落地生根、开枝散叶的念头,而不想再流浪了。任嚣、赵佗都是从北方来了就不想走的;广州十三行行商中,有10家祖籍福建,他们的祖上在来广州之前,也不过是碌碌庸流,但一到广州,便如飞龙在天,鱼跃大海,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试问有谁听过伍秉鉴、潘振承、吴天垣、谢有仁,或任何—个十三行富商抱怨广州人排外的?
改革开放以来,广州又为无数怀着美好梦想南下创业与谋生的人,提供了天高任鸟飞的平台。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来说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的外来人口,分别为282万、319万、318万,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20.0%、19.4%和30.0%。广州外来人口的比例,说广州排外,它排谁了?
按一般逻辑来说,—个严重排外的地方,应该没什么外来人口,即使有也难以进入主流社会,但看看今日的广州,在主流社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外地人还少吗?奇怪的是,愈是城门大开、五方杂处的城市,愈容易招来排外的非议;外来人口愈少的地方,反而愈没人骂它排外。搬个小板凳往家门口一坐,三街六巷全是俺乡里乡亲的,啥子叫排外哟!没听说过!
其实,广州人并不排斥外地人,川菜、湘菜、鲁菜、粤菜、泰国菜、葡国菜,在这个城市都能各随所好,一荣俱荣,有钱齐齐揾;客家人、潮汕人、广府人、北方人要和睦相处,也不是什么难事,只要互相尊重,平等相处就行了。南越王赵佗是河北人,但他尊重岭南本土文化,推行“百越和集”和“变服从俗”的政策,广东人便尊他为岭南的人文始祖。这叫你敬人一尺,人敬你一丈。
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国衣冠,文化使者,别人都是蛮貊鸟语。广州公交用粤语报站,你就说是歧视外地人;广州媒体把贝克汉姆译成碧咸,你又说这是对北方文化缺乏包容。样样都看不顺眼,到底是广州人排外呢?还是某些不了解广州的人在“排穗”、“排粤”呢?须知世界是多元的,文化也是多元的,大家都有保持自己方言和生活习俗的权利。如果一味以蛮横的方式扰乱别人的生活,硬是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,谁不接受谁就是排外,也未免太霸道了吧?
恩怨分明的广州人
以往人们在谈论十三行时,往往只说它如何崛起,如何昌盛,却很少谈论它是怎么消失的,或者只是含糊地用一句“毁于鸦片战争的炮火”轻轻带过。其实十三行是广州人自己放火烧掉的。
广州人有一种恩怨分明、宁折不弯的性格。在全国城市中,广州与海外通商时间最长,如果广州人排外,就不会有十三行了,就不会成为“金山珠海,天子南库”了。我们看看近代史,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,鸦片战争前,广州对来做正常贸易的外商,不管他是欧洲人、波斯人,还是南洋人,大门都是敞开的,所以才会出现“洋船争出是官商,十字门开向二洋。五丝八丝广缎好,银钱堆满十三行”的盛况。美国商人亨特在《广州番鬼录》中也承认,由于在广州做生意很便利和广州人“众所周知的诚实”,让外商“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”。
但鸦片战争后,广州人突然收起了友好的姿态,来了个180度大转变,站到了抵抗外国侵略的最前沿,不仅一把火烧了十三行,而且还发起了长达20年的反洋人入城斗争,万众一心,牢不可破,决不让洋人再踏进广州一步。
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?难道这些反入城的广州人,不是当初在珠江岸边热情招待洋商的广州人了吗?
城还是那座城,人也还是那些人,变了的是洋人,不是广州人。这时的洋人,已非当初坐着哥德堡号来做买卖的茶叶商、瓷器商、丝绸商了,他们带来了鸦片,带来了掠夺和欺凌,带来了战争。这一切侵略恶行,已为天下人所共知,这里亦无须再一一赘述了。因此,不是广州人不想赚钱了,不是他们灵活的生意头脑突然不灵了,也不是他们忽然盲目排外了,而是广州人就是这么“硬颈”(犟),宁愿一拍两散,不做生意了,也不让你*计得逞。洋人百般无奈,只好纷纷改到上海做生意,上海才有机会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埠。
广州人的举止看上去好像很蠢,竟然自砸饭碗,把这么好的贸易基础毁了,把这么大一座金矿拱手让给上海。但是,如果他们为了继续做生意,就忍气吞声让洋人进城,就不叫广州人了。他们守护家园、捍卫民族、国家、文化命脉的决心,就是如此坚强,如此不惜代价。有些当代学者,批评当年广州的反入城斗争是盲目排外。依我所见,决不是一句“盲目”可以概括得了的。它是当时具体的政治、社会背景、文化背景和广州人性格碰在一起,所发生的必然反应,不能仅以今天的纯法理观点去评判功过。否则,连废除不平等条约,恐怕也会因缺乏法律依据,而成为“盲目排外”的证据了。
今天,广州人既没有、也不会盲目排斥外地人,最近有人提议限制“低素质人群”进广州,结果引起轩然大波,人人群起而攻之。其实,大量贫穷人口涌来广州,最该受到舆论谴责的是输出大量贫穷人口的地区政府,他们不好好解决老百姓的生计问题,却把责任转嫁给别人,但现在没有谁去批评他们,反而纷纷责备广州为什么不能接纳更多的外来人口。须知一个城市的容量是有限度的,资源也是有限度的,如果超载了,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。这与道德无关,与良心无关。广州治安恶化,恰恰证明它已经出现超载问题了,资源的短缺,最后必然会引起暴力争夺。
凡是来正当创业、打工的,广州无条件欢迎。广州人所痛恨的是那些来打家劫舍、偷讹拐骗、作*犯科,破坏他们正常生活秩序、破坏他们家园的害群之马。你和老百姓空谈什么社会学的公平理论没有用,他们所见所闻,在广州犯案的不法分子,八成是外来人员,这是一个铁板钉钉、无法否认的事实。再好客的人,也不可能要求他欢迎强盗吧?
人们习惯于一说外来人员就是“弱势群体”,但如果没有制度的保护,广州人也强势不到哪去。几年前,有几个广州人敢在火车站流连?每当我看见那些被飞车抢夺后,坐在马路边无助痛哭的广州市民时,我就会想:这些就是所谓的“强势群体”了吗?
说到底,“排外”问题的根子,并不在普通广州人那儿,而在于制度。一个城市能否让人安居乐业,有没有一个和谐的环境,归根结底是一个制度问题。有了完善的城市管理制度,人们自然可以各安其位,各尽其责,各得其所。与其一味责备广州人排外,不如多想想怎么改善我们的管理制度吧。